往事不如烟,记反殖岁月轶事系列2: 以今评古恐失偏颇 一切 皆时代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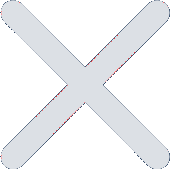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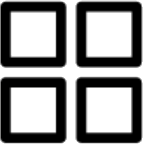

何俐萍/报导
ADVERTISEMENT
前言:
六七十年代是砂拉越左翼运动最风风火火的阶段,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参与反殖反帝的斗争,也为了追求砂拉越独立的梦想,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有者甚至搭上了宝贵的性命。这场持续将近28年的运动是时代的产物,也因为形势发展使然,终归一句是“时不予我”而以失败告终。

死去的人留下“烈士”之名,活下来的人当中,有的在扣留所拘禁了数年的时光,重新踏入社会时已是人事已非,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后悔参与吗?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领袖黄纪作很多年在在一次的访谈中,我曾追问他是否后悔时,他以一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淡然回应。时光一去不复返,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当时的抉择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和际遇,所历经的一切都写在他们生命的篇章中。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当年持着不算新颖的武器,还徒步到边界接受军训以准备进行武装斗争者,也许你无法理解他们的思维,甚至还觉得有些可笑。但公正客观而言,处身在当年追求独立的大浪潮中,受大环境影响,也许你我在情感上也会受到感召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也并不能形容为愚蠢,只是形势的逆转和客观条件的种种不利,他们必须直面现实,接受这条斗争了二三十年的路并不可行的最终结局。

口述历史记录过去
人命的牺牲影响的不只是个人,他们当中有些家庭也承受一夕天伦梦碎,后代对他们唯一的印象也许只是挂在墙上的那帧遗照。回首走过的路,当年参与武装斗争运动者不是已离开人世,就是已垂垂老矣,搁下立场,不纠结于谁是谁非,透过口述历史,至少从一些细节中,让我们知道上一代的人经历过些什么。
打6年游击战 被扣2年 贝雄伟年过30再重来
贝雄伟(83岁),砂拉越福利协会主席,当年也打了6年的游击战,尔后又被扣留了2年,重新投入社会时已年过30,与社会脱节多年的他,一切得重新来过。

询问他是如何看待当年的斗争运动,他边翻阅剪报边喃喃自语说道:“这是不‘Jadi’(意即不成)的事”。最初,武装斗争得到印尼政府在军事支援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在苏卡诺政权倒台,苏哈多上台后,情势大逆转,在两面夹攻的不利局面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也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贝雄伟的车房一隅俨然如他的小书房,从桌面到书架都是一叠又一叠的资料,有他这些年发表过的言论剪报,也有他这些年收集的“老朋友”资料。那些因斗争而牺牲被迫埋尸荒野的战友都被他一一记录在簿子上。“老朋友”、“老同志”敌不过岁月,成员是有减无增,谁在某年某月某日离世,他都详尽记录,那一笔一划道尽深埋心中的感慨。

贝雄伟,又名贝永庭,出生在晋连路29哩半一户椒农的家庭。革命思想的种子在当年在农村觅得土壤播种并茁壮成长,长期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贝雄伟也因一股热血,被招揽进入组织,开始负责农运的地下组织工作。也因为他的活跃,自然被盯上,成为警方黑名单中的其中一号追捕的人物。
受伤生病 只能自救 1963年走到印尼军训
1963年6月间他被征召越境到印尼接受军训,服从命令的他第二天就带着简便的行囊到组织指定的地点集合,也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去就是6年。到印尼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巴士或私家车,而是靠自己的一双脚,贝雄伟当时和逾60名的青年男女在组织“交通员”的引领下出发,徒步穿越山林来到巴达旺山区的甘榜苏禄,休息一晚后,再从打必禄越过边界进入印尼境内的恩帝贡(Entikong)。地下组织成员都不会用真名真姓行事,贝雄伟在部队内就采用“方明”这化名,至今还有一些人称呼他为“老方”。
在部队的训练下,贝雄伟学习基本的射击和和游击战术,也被提拔为干部级的小队队长。然而,他们使用的枪械属于二战期间使用过的老旧枪械,不但射程近还常有卡弹的危险,贝雄伟有数次在驳火中在紧要关头时卡弹,险些性命不保。

赤脚打游击战
为避免轻易被侦察到及行踪暴露,在山林打游击战的那几年,贝雄伟一直是赤脚,纵使地上长满带有尖刺的籐类植物他也照踩不误。也因为多年都是赤脚走,他的脚底结出了一层厚茧。曾有过来人告诉我,一些游击队员则是故意把鞋子倒反穿,这是误导敌方的其中一种心理战术,让敌方依循错误的足迹去追踪。
深居山林,不管是生病了还是受伤了,也得靠自救。贝雄伟有一次在开芭砍树时,就被回弹的利刀劈中左脚,左脚掌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有人就地找来不知名的草药为他敷药及包扎,伤口在数天后逐渐愈合,但他的脚掌自此留下一道清晰的疤痕。此外,游击队队员几乎都逃不过感染疟疾,一旦染上最苦恼的是不时复发,难以断根。贝雄伟也被疟疾纠缠多年,他是直到后期返回古晋被送到中央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才痊愈。
长期忍饥挨饿 逝者只能草草埋葬
“改善生活”这词是游击队员用来形容“加菜”,山林不缺珍禽异兽,那个年代也没有所谓的受保护动物,自然也没有法令的箝制,游击队员也不时射击到野味,生火烹调大快朵颐一番就是最欢乐的时光。
靠山林动物“加菜”
一回,贝雄伟和队员以为遇上敌军突击,举枪循“斯斯声”查看时,不见敌人倒见两尺长的白蟒蛇,他立即动作利落拔刀往蛇头狠刺。就这样,白蟒蛇成了队员们成为当天加菜的盘中餐。
山林中的生活不是写意轻松的,除了一些在斗争中牺牲于枪林弹雨中,也有些青年男女是因不适应林中的生活,因受伤、感染或生病而病死在林中的也不在少数。碍于身份的敏感,他们不是被草草埋葬,就是在队员慌乱逃离时因顾不上,不得已被弃尸荒野,后期在失去印尼军方的支持后,有者还被残暴杀害 ,包括被砍头。
印尼军方从支持到枪口对准游击队队员,加上大马的辜加兵团也在追击他们,他们的处境愈加艰难,不但生命受到威胁,对外通讯被中断,储粮的仓库也被焚毁,最难堪的是来自砂境内的援助也受影响,不但要断粮、断药,甚至陷入连食油和盐都没有的窘境。为了求生存,队员们只能靠野生蔬果,甚至是腐烂的果实来果腹。

遭印尼兵伏击成俘虏 再见双亲恍如隔世
1969年年底,贝雄伟和一名战友在打必禄边境的山林执行巡逻任务时被一早埋伏的印尼兵俘虏,之后被押送交给警方发落。被俘虏时,贝雄伟等人已经一年多没吃过油盐烹调的食物。因为受到双面夹攻,许多队员不是战死、病死就是饿死,士气低落。

贝雄伟6年未见父母,再见面时是身处在6哩的政治犯扣留营,彼此再见是恍如隔世。被关在小小的黑暗斗室中,回首自己在森林斗争的岁月是感触涌上心,也不仅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离开扣留营重新生活
离开扣留营后,贝雄伟当过流动小贩,也做过小生意,日子虽然平淡但也过得踏实。后来他成立砂拉越福利协会,目的是联系当年因政治因素而被拘留的老朋友,90年代和平协议的签订,砂拉越迎来睽违已久的和平,而“老朋友”的人数也在岁月无期的洗礼下逐渐减少,或许终将有一天也将走入历史。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
































